南极土著:《反外国制裁法》在“芯片战争”中的首次出手
【文/南极土著】
近日,对美国意图封杀华为昇腾等中国先进计算芯片的guidance(“指导意见”),中国政府进行了严正回应。
5月20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交部长王毅在京会见美国亚洲协会会长康京和时指出:
美方继续遏制打压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,近日竟然试图对中国芯片进行全面封杀,这是赤裸裸的单边霸凌,中方坚决反对。
5月21日,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:
中方强调,美方措施涉嫌构成对中国企业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。任何组织和个人执行或协助执行美方措施,将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》等法律法规,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美方通过guidance明确使用华为昇腾芯片可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。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的上述表态则相当于明确:如因慑于美国出口管制法规而“执行或协助执行”上述guidance,将涉嫌违反中国的《反外国制裁法》。
根据《反外国制裁法》第12条:
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、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。
组织和个人违反前款规定,侵害我国公民、组织合法权益的,我国公民、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其停止侵害、赔偿损失。
根据3月份第803号国务院令“实施《反外国制裁法》的规定”:
第十七条 对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、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,国务院有关部门有权进行约谈,责令改正,采取相应处理措施。
第十八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、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,侵害我国公民、组织合法权益的,我国公民、组织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要求停止侵害、赔偿损失。
换言之,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发布的这个“guidance”属于“歧视性限制措施”,受到《反外国制裁法》约束,“执行或协助执行”该guidance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可能违反该法律,具体包括以下两类法律风险:
1、行政处罚:可能会被中国政府采取约谈、责令改正等行政措施,甚至其他处罚;
2、被提起侵权诉讼:因相关企业的“执行或协助执行”而受损失的企业,基于《反外国制裁法》获得了一个民法上“侵权之诉”的诉权,现在可以依据《反外国制裁法》直接把“执行或协助执行”上述guidance的企业告上法庭,要求停止相关行为;如因此遭受了损失,还可以要求相关企业赔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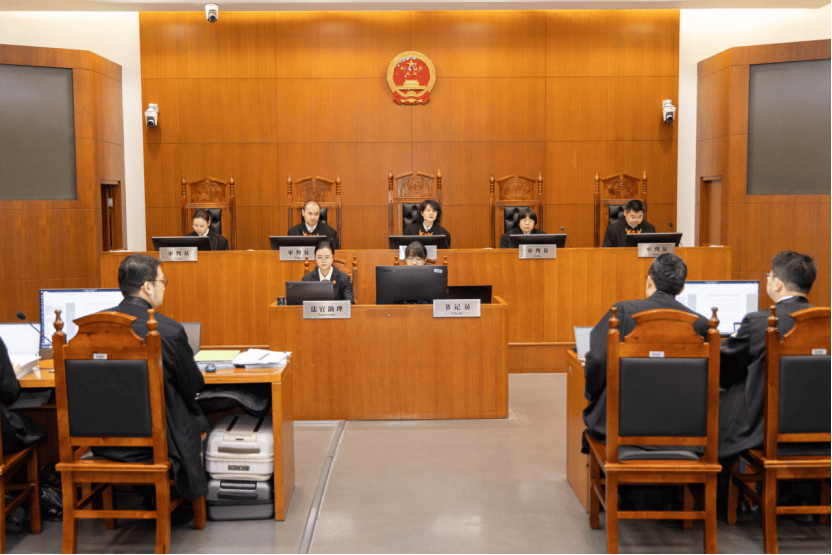
资料图来源:上海一中院官网
什么样的行为才算“执行或协助执行”,《反外国制裁法》及后来的实施规定都没有阐明具体标准,也让第12条变成了一个政策性很强的条款,实践中会衍生一些操作层面的问题:
例如,如何认定一家中国公司暂停采购国产先进计算芯片,是出于自身项目调整、业务转型等商业考量,还是因为担心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?在和供应商或客户的合同中加上一句遵守美方guidance的约定,是否有被认定为“协助执行”的风险?考虑到guidance带来的风险,企业开展一些合规调查或风控动作,是否属于“协助执行”?
自2021年出台以来,对《反外国制裁法》第12条的执法实践极少。有据可查的只有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两会工作报告披露的一则案例。
2023年,某中企为一个欧洲企业建造海上浮式储油船水处理模块,项目建成交付后,该中企被美国财政部以违反涉俄制裁为理由列入SDN清单,其欧洲客户以“遵守美国制裁”为由拒付近亿元尾款。该中企随后在国内起诉,援引《反外国制裁法》和商务部《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》,成功促使涉案欧洲企业推动美国财政部出具许可,并最终全额付款。
尽管如此,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作出相关表态之后,美国的《出口管理条例》(EAR)中的“一般禁令10”和中国《反外国制裁法》第12条,还是构成了正面冲突。
这意味着:全球任何企业,包括在中国境内运营的外资企业或中国本土企业。只要遵守美国关于昇腾等中国高性能计算芯片的“guidance”,就有可能被认定违反《反外国制裁法》第12条。
与欧盟的“阻断法”不同,《反外国制裁法》第12条没有设置“豁免机制”(Waiver System)。因此对所有受影响的企业来说,面对这个中美法律的直接冲突,还没有法律上可行的解法。
在中美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,G2不断强化各自的制裁和反制裁机制。由于两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强大影响力,这些法律不仅适用于本国,也展现出很强的域外效力。越来越多中美企业夹在本国制裁法和对方反制裁法之间,面临无论如何都会违反一方法律的两难困境。由于美国经济制裁的“次级制裁”机制,第三国和中国做生意的企业有时也无法幸免,可能受到美方“次级制裁”和中国针对性反制裁的影响。
不过,上述法律冲突的状态,有时也为企业带来一些抗辩的理由。
